南柯梦(三十七)
浮生若梦欢几何,群季俊秀幽赏游
香心淡薄独咏歌,春风拂槛露华浓
曾记得在曹家府上闻鸡鸣而起忽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如今踏入禅房花木深的萧然佳色的古寺。泪水从晶亮的眸子滑落,在白玉一般的面孔上划出的痕迹,竟是那样的动魄惊心。春色依然潜心过目。愁病交集再次复发,根无可遣,终日在药炉茗碗间消磨岁月,颇觉自苦,聊借此以遣病魔。
春儿听见我随着一声疼痛无可奈何的叹息的动静,忙搁下手中的活儿趋前道:“香玉妹妹刚生病痊愈不久,身上的淤血未尽,气脉虚弱。今日又车马劳顿一番折腾,怕是有些不好。”她急道:“炉子上的水还未开,还须找些大枣肉桂来熬水兑了热热的喝下去才好。看来不能轻易受寒在外面闲走。”
我心下发急,又要强,少不得道:“这荒山野岭的,一时半刻哪里来的大枣肉桂,我忍一忍兴许会好了。”
彩云忙道:“妹妹旧疾复发的毛病不能掉以轻心,若不及时治愈弄不好要落一辈子的病根的。”说着起身,道:“奴婢这就去向隔壁的小妮子们借些应付缓缓过去。”
说着披衣出去,春儿忙扶了我上床躺下,多多地盖了几层棉被防寒侵身。我心下焦躁不安,寺中的生活凄风苦雨自然比不得宫中安逸舒适,我身体还未复原,反倒牵连了春儿和彩云处处照顾我,如此想着,心脾更生疼痛。
本想起身喝水却没想到刚刚抬起一些的身体又一次重重地砸到坚硬难睡的床板上。痛苦的呻吟在咽喉里徘徊了一下,还是被惊人的自制力强忍了回去。只好那样地躺在冷若冰窟的床中,看着窗外茂密的枝叶和一点一点露出来的深邃的夜空,四肢怎么还是断了似地一点力气都没有。
神思微微有些恍惚的误以还在幸福无忧中享受一切,沉静淡然一如往昔的欢声笑语梦影早已云淡风轻。泪竟是不能自抑。
在充满温馨暖意的家里,曹颙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为我的旧疾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守在病床边看着几日几夜未眠。从十里长街寻遍医馆请医疗治。漫长的一月光景方渐愈,身体劳倦,年纪又小,身体又极怯弱。亲生的母亲过世较早,在母亲生病后,整日守候在身边,奉侍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旧病复发。
自从那日起,由于哀痛过伤,本自怯弱多病的,触犯旧症。整个人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失去在家一切感觉都成往事如烟的笑容,默默含笑无论如何,镜花水月。过眼皆空;海市蜃楼。到头是幻。
静躺在床上回想着家中幸福的日子,不只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响了,料是彩云回来了,语气无奈道:“夜深人静怕是都安然入睡了,无人愿意开门见客,别说借些大枣肉桂了。”她的声音更低沉:“我去寻*师太,还被她训斥了两句,只是暂时还未敢惊动住持慈安师太。”
春儿以为我熟睡了,低声叹息道:“方才住持师太还说是仿着从前清世祖的先例来,无论如何从面色看还是气色看师太四处彰显慈爱仁厚,作为佛门弟子也极力表明自己慈悲为怀。可一转身就连热茶热水也没有了。”
我隐约伴着朦胧迷糊中听着,心下更是难过飒然间看清了世事无常。
忽然彩云似想起什么,搓一搓手喜道:“在我回来的路上,发现那边远处大树下独有一间飘满药香的屋子,也不知是哪位师太住着,我再去寻一寻看。”
春儿听后面色有些惊恐,但还算冷静忙拦住了道:“傍晚出门打探听两个打水的小尼姑说,那里住了个脾气极古怪的尼姑,平时无人敢搭理招惹她。还是再去另寻别人那里问问。”
彩云苦闷道:“其他的都去了,方才不愿意开门出来见客,现在只怕更不愿意了,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还是为了主子着想先去看一看再说。”说着又嘱咐道:“水烧开了再烧上一壶,方便香玉妹妹擦洗身子。”
略微地停顿后便转身出门外。彩云自己竟微微又发起抖来,面色突然变得苍白。
“难得彩云妹妹有这份心,尚且小心!”春儿担心不悦,眉头皱起。再三叮嘱道。
无数种感情一瞬掠过心头,彩云还没回来,我身上更觉得阴冷。深悟归家的企盼难得可贵,这样的日子不会有人帮我,我只能自己珍惜自己。命虽如草芥,却未必要舍弃。忽然听得门“砰”一声被用力踢开。一阵冷风夹着一个雪白的人影霍然坦荡地闯了进来,落泪如雨紧握我手心的春儿还用情之中,还未惊住,本想开口问道:“请问阁下是谁?!”
还未说出,那人也不答话,直奔我床前,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搭了搭脉,姿势粗鲁而利索,片刻望着我冷声冷语道:“你动情至深,余意缠绵,心脾潮热,经常轻咳,时常头晕,是不是?!”
我挣扎着仰起头来,只见那人眼神令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歧视、寂寞、排斥和放逐,苍凉的心境。让我都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她还是一个刚刚二十几岁带发修行的韶龄女子。长得倒也有几分姿色,只是那姿色都随着内心变的惊人的冷漠和孤僻如严霜被冻住了,神情十分气定冷淡。窗外蔓延的万里晴空突然像是被打翻的墨汁染了般,骤然压了下来,眨眼间阴雨坠落,丝丝的滴在脸上。下雨了。我看她一身尼姑清新打扮,想必也是寺中的同门,遂示意彩云不要惊恼心灵默契的境地,勉强道:“是。我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
她没有说话,修长的手指轻轻抚着我的锋芒,看着面前惊疑的众人,眼睛里有讽刺的光。然不知为何轻轻“哼”了一声,神情大是不屑,道:“听闻你一个姑娘家措辞文雅大方得体,正是你在宫里一向风高气傲的时候。何苦来这荒山野寺做什么!活活受这番罪!明日清晨回去吧!”说着丢下怀中一包不知是何物的东西掷在床头道:“唉!这些足够你喝到好为止了。”
我听见从未有过的微弱、但是极具威势的声音在阵阵寒风耳边响起来,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刻薄安慰之声。一时间,凝结的气氛仿佛又加上了令人屏息的静穆。
彩云忙接过一看,喜形于色:“太好了。是大枣肉桂!怕是足有三四斤呢。”
那清逸脱俗的女子也不吭声,又掏出几片罕见的西洋参,命我含在口中,道:“熬水喝下,这东西能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增智。”
“但是?”春儿竟在这时插话,却话音渐弱。
“但是什么,有话就要快些说。”这位突如其来的女子的心似乎漏跳了一般,隐隐感到了还有不解的地方。
“但是,主子娘娘常年反反复复这样吃了这几份药是否会见效,会痊愈如初呢?”春儿面上虽有些怯懦,却说出一句让众人都惊讶的话来。
“这些药只能舒缓病情,治标不治本!欲要痊愈如初只能看姑娘的造化了,还要从心治。”女子显得焦急不耐烦,提高了声量回答。
说完似在生谁的气,气冲冲地又一阵风似的走了。

 [小说]如何让我遇见你
[小说]如何让我遇见你 [小说]绝世护花高手
[小说]绝世护花高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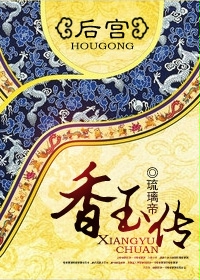 [小说]后宫香玉传
[小说]后宫香玉传 [小说]豪门甜心:征服撒旦老公
[小说]豪门甜心:征服撒旦老公 [小说]纪少,你老婆超甜的
[小说]纪少,你老婆超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