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阶怨(四十五)
帘外雨潺意阑珊,梦里不知身是客
流水落花春去也,残酒欲醒中夜起
那日,宋春书与郑亲王等,尽享在郑亲王府内的怡园作消寒赋诗之会。
在郑亲王怡园之事中:有个柔美公子领头,文人领袖,姓阮名灏君,号芳玉,是苏州如皋人。
说他家世,真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七世簪缨之内,是祖孙宰相,父子尚书,兄弟督抚。
单讲这位阮灏君的家世,其父名震,由翰林出身,现做了大学士,总督两广。是郑亲王爱新觉罗奇通阿深交,其兄名舒玄,也是翰林出身,由御史放了淮扬巡道。
其太夫人随任云南去了,单是灏君在京。这灏君生得温文俊雅,卓荦不群,度量过人,博通经史,现年二十出头。
由一品萌生,得了员外郎在部行走。不久之前又中了一个举人。夫人安氏,年方十九岁,是现任河南巡抚安阔之女。生得花容绝代,贤淑无双,而且蕙质兰心,颂椒咏絮,正与灏君是瑶琴玉瑟,才子佳人,夫妻相敬如宾,十分和爱,已生了一子一女。
这灏君虽在繁华富贵之中,却无淫佚骄奢之事,厌冠裳之拘谨,愿丘壑以自娱。
虽二十岁人,已有谢东山丝竹之情,孔北海琴樽之乐。他住宅之前,有一块大空地,周围有五六里大,天然的崇丘洼泽,古树虬松。原是当初人家的一个废园。
灏君买了这块空地,扩充起来,将些附近民房尽用重价买了。
曾记得他有个好友,是西域随父经商入京,姓简名玉珩,号静轩,年方二十二三岁,是个名士,以优贡人京考选。他却厌弃微名,无心进取,天文地理之书,诸子百家之学,无不精通。与灏君八拜之交,费了三四年心血,替他监造了这个怡园。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驱云排岳之势不可阻挡,祟楼叠阁之观亦不甚惜,炉火纯青非以鬼斧神工可比。
一时花木游览之盛,甲于京都。成了二十四处楼台四百余间屋宇,其中大山连络,曲水湾环,说不尽的妙处。灏君声气既广,四方名士,星从云集。
但其秉性高华,用情恳挚,事无不应之求,心无不尽之力,最喜择交取友,不在势力之相并,而在道义之可交。
虽然日日的座客常满,樽酒不空,也不过几个素心朝夕,其余泛泛者,惟以礼相待,如愿相偿而已。
京城嫡庶之汤黎璇《南柯记》中的九个名花旦日夕来游,灏君尽皆珍爱,而尤宠异者惟凤紫菱。这一片钟情爱色之心,却与别人不同,视这些好女子与那奇珍异宝、好鸟名花一样,只有爱惜之心,却无褒狎之念,所以这些名花旦,个个与他忘形略迹,视他为慈父恩母。
甘雨祥云,无话不可尽言,无情不可径遂。那个墨紫薰更是清高恬淡,玩意不留。
故此两人,不独以道义文章交相砥砺,而且性情肝胆,无隔形骸。
一日,阮灏君在堂会中,见了新来的芳官、蓉儿两个,十分赞赏,叹为创见,正与那九个名花旦一气相孚,才生了物色的念头。叫凤紫菱改日同他们到园来。
又见他们的服饰未美,即连夜制造了几套,赏给了他们,这两个戏子自然感激的了。但那个芳官,却又不然。且先将他的出身略叙一叙。
这个芳官姓渝,父亲叫做渝芳溪,以制琴弹琴为业,江苏绅子弟争相躬请教琴,因此世人称他为渝琴。生了这个儿子就以芳字为名,叫为芳官。
琴官手掌有文,幼而即慧,父母爱如珍宝。到了十岁上,渝琴忽为豪贵殴辱,气忿碎琴而卒。
其母一年之后,亦悲痛成病而死。遗下这个芳官无依无靠,赖其族叔收养。十三岁上叔叔又死,其婶不能守节,即行改嫁,遂以芳官卖入梨园。
适戏师吴昆生见了,又从戏班中扎实练唱戏,同师傅和蓉儿进京。这芳官六岁上,即认字读书,聪慧异常,过目成诵。
到十三岁,也读了好些戏曲文苑书,以及诗词杂览、小说稗官,都能了了。心既好高,性复爱洁,有山鸡舞镜、丹风栖梧之志。
当其失足梨园时,已投缳数次,皆不得死,后遇到龄官蓉儿。所以本想厌弃已久,芳官借以自完。及一人居于京,顿为薰沐,视如奇珍,在人岂不安心?
他却又添了一件心事:以谓出了井底,又入海底。犹虑珊网难逢,明珠投暗,卞珍莫识,按剑徒遭,因此常自郁郁。
到京前一夕夜间,做了一梦,梦见一处地方,万树梨花,香雪如海。正在游玩,忽然自己的身子,陷入一个坑内。
将已及顶,万分危急,忽见一个美少女,玉貌如神,一手将他提了出来。芳官感激不尽,将要拜谢,那个少女翩翩的走入梨花林内不见了。芳官进去找时,见梨树之上,挂着一条大玉带,细看是玉的,便也醒了。
明日进京城,在路上挤了车,放佛一闪见了红玉,就是梦中救他之人,心里十分诧异,所以呆呆看了他一回。但陌路相逢,也不知他姓名、居处,又无从访问。
如寻遍紫禁成内外,四下留心,也没见她。后来见了阮灏君,十分赏识他,赏了他许多衣裳什物,心里倒又疑疑惑惑。又知道是个贵公予,必有那富贵骄人之态,十分不愿去亲近他。无奈迫于师傅之命,只得要去谢一声。
是日蓉儿感冒,不能起来,墨紫薰先到芳官寓里。这个紫薰的容貌,《南柯记》中已经说过了,性阳柔,貌如处女。
她也爱这芳官的相貌与己仿佛,虽是初交,倒与夙好一般。两人已谈心过几回,芳官也重紫薰的人品,是个洁身自爱的人。
紫薰又将灏君的好处,细细说给他听,芳官便也放了好些心。二人同上了车,芳官在前,宝珠在后,正是天赐奇缘,到了胭脂胡同口,恰值灏君从汤黎璇处转来,一车两马,劈面相逢,灏君恰不挂帘子,芳官却挂了帘子,已从金丝窗内,望得清清楚楚。
不觉把帘子一掀,露出一个绝代花容来。灏君瞥见,是前日所遇、聘才所说、朝思夕想的那个芳官,便觉喜动颜开,笑了一笑。见芳官也觉美目清扬,朱唇微绽。
又把帘子放下,一转瞬间,各自风驰电掣的离远了。灏君见他今日车袭华美,已与前日不同,心里暗暗赞叹:“果信夜光难掩,明月自华,自然遇了赏鉴家,但不知所遇为何等人。”
又想:凤紫菱说他脾气古怪,十分高傲,想必能择所从,断不至随流扬波,以求一日之遇。
这边芳官心里想道:看这公子其秀在骨,其美在神,其温柔敦厚之情,粹然毕露,必是个有情有义的正人,绝无一点私心邪念的神色。
我梦中承他提我出了泥涂,将来想是要赖藉着他提拔我。不然,何以梦见之后是否就遇见了他。但那日梦中,见一翘美公子走到梨花之下就不见了,倒见了一个玉带子,这又是何故呢?”只管在车里思来想去,想得出神。
不多一刻进了郑亲王怡园,凤紫菱询知灏君今日在碧海棠春。这碧海棠春,平台曲榭。密室洞房,接接连连共有三十余间。紫菱引了进去,到了三间套房之内,灏君正与紫薰在那里围炉斗酒,见了这二人进来,都喜孜孜的笑面相迎。
芳官羞羞涩涩的上前请了两个安,道了谢,俯首而立。灏君、紫薰见他今日容貌,华装艳服,更加妍丽了些。但见他那生生怯怯、畏畏缩缩的神情。教人怜惜之心,随感而发,便命他坐下。
芳官挨着紫菱坐了,灏君笑盈盈的问道:“前日我们乍见,未能深谈,你将你的出身家业、怎样入班的缘故,细细讲给我听。”
芳官见问他的出身,便提动他的积恨,不知不觉的面泛桃花,眼含珠泪,定了一定神,但又不好不对,只得学着官话,撇去苏音,把他的家世叙了一番。说到他父母双亡,叔父收养,叔父又没,婶母再蘸等事,便如微风振箫,幽鸣欲泣。听得灏君、紫薰,颇为伤感,便着实安慰了几句。

 [小说]绝世护花高手
[小说]绝世护花高手 [小说]邪王追妃:废材逆命二小姐
[小说]邪王追妃:废材逆命二小姐 [小说]如何让我遇见你
[小说]如何让我遇见你 [小说]寒门驸马
[小说]寒门驸马 [小说]纪少,你老婆超甜的
[小说]纪少,你老婆超甜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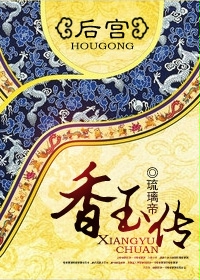 [小说]后宫香玉传
[小说]后宫香玉传 [小说]豪门甜心:征服撒旦老公
[小说]豪门甜心:征服撒旦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