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5章
姜灼坐到孩子对面,示意乳母将脸背了过去。
乌黎不解其意,一眼不眨地在旁边瞅着,倒是秦宴似乎明白了些,抱着双臂立于床前。
眼瞧着姜灼从火盏抓起一把药末,摊在手心,靠着孩子近了些,再然后,便冲着他面门吹了一下,药末立时扑到孩子脸上,因这药多取自花草,被姜灼这么一吹,不免满屋含香。
乳母一脸的迷惑,实在是姜灼这治病的手法,竟像是在玩笑一般,倒是姜灼并不肯停,冲着孩子吹了好一时,那火盏之中,竟下了一半的药末。
“啊嚏”一声,那孩子突然之间竟有了动静,姜灼并未防备,以至于手中半盏药末,竟是直吹到了她的脸上。
随后,孩子又喷嚏了四五声,这边姜灼从床站起,取过身上的帕子,拭去头上脸上的药末,转头对乌黎笑了起来:“成了!”
果然,不一会乳母叫起来,原来孩子竟然睁开了眼,不过随即,便开始吐出稠痰。
秦宴瞧瞧左右,顺手拿了个漱盂,递到孩子口边。
等到吐了半盂,姜灼取来茶盏,让孩子漱了漱口,再见他已然完全清醒,打量了自己好几眼,转头瞧向乌黎,叫了一句什么。
此刻乌黎脸上全然是喜出望外,上前将儿子一把抱在了怀里,使劲搂了搂,姜灼似乎瞧见,他眼圈竟有些红。
“乌黎大人,令公子歇息数日,便可痊愈了。”姜灼在一旁道。
“多谢!”乌黎将儿子放下,冲着姜灼点头:“本官言而有信,明日便携子,与你等一同去长安城,此后为奴为婢,任由支使。”
这话让姜灼听心里一揪,不由看了看此时半坐在床上的孩子。
乳母这会子在孩子耳边说了些什么,那孩子竟一直在瞅着姜灼,神色中是好奇和探究。
姜灼同秦宴走出抱厦,见李郡守还在,少不得向他复了命,只说孩子已经无恙,过不得几日便能痊愈。
李郡守立时表情松快下来,冲着他们一拱手下,转身便往外走,想来是给诸葛曜报信去了。
姜灼猜测,无论诸葛曜还是他的那些近臣,怕是个个都在盼着乌黎乖乖投降,看来那位小郎平安与否,竟是牵扯着朝政大事。
瞧着李郡守走远,姜灼同秦宴两人便由郡守府的奴仆领着,一块往外头走去。
“我可听说过,那乌黎乃是耶律拓身边近臣,说起来,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回虽未抓到耶律拓,逮了一个乌黎,也是桩不得了之事,将人带回京城,自是鼓我士气。”走到垂花楼下,秦宴望了望身后,不由感叹起来。
姜灼对乌黎到底投不投降倒不在意,只方才瞧那个孩子,想着稚子无辜,竟要与其父一同做了俘虏,从此流落异乡,也不知日后是何下场,不免为这孩子感到唏嘘。
秦宴瞧出了姜灼神情中的悲悯,不赞成地道:“姜太医莫非在同情他们?可知当日,若耶律拓阴谋得逞,与王巍勾结攻进咱们大靖,说不是不但皇族,便是咱们这些人,也得成了亡国之奴,想来那时候,可没人同情咱们。”
姜灼少不得解释了一句:“我只是觉得,无论如何罪不及妻子,便是乌黎有罪,难道还得让女人孩子,也跟着他被押上囚车?”
荀成还在门外站着,此时正跟几名兵将模样的人聊得热络,见姜灼二人出来,少不得蹦上前来,问道:“师父、秦太医,可是那个匈奴小崽子给救好了?”
“什么小崽子,哪有你这般说人的。”姜灼瞪了荀成一眼,便自先上了车。
等秦宴跟着上了车,荀成也坐到前头,不慌不忙地赶着马,道:“大家伙可都听说了,这一会陇西王立下大功,擒获耶律拓身边近臣乌黎,说是此人当初在匈奴势力极大,谁都要给他三分颜色,不过后来树倒猢狲散,新任单于更是厌恶此人,当日占了王庭之后,一道旨意便杀了乌黎府中上下几百口,那会子乌黎正跟着耶律拓在白亭海坑咱们圣上呢!”
姜灼往车外靠了靠,问:“后来怎得乌黎之子得了救?”
“谁还没几个忠心的手下,乌黎这么大岁数,千倾地一棵苗,就只得这一子,自是百般珍惜,后来他跟耶律拓从白亭海逃回匈奴王庭,耶律拓大势已去,乌黎也顾不得别的,只管着要找着儿子,后头干脆一走了之,听说是与耶律拓两人最后起了龃龉,就此分道扬镳,一个不知下落,一个便偷偷进了咱们大靖。”
“荀成,你这消息倒是灵通!”秦宴笑道。
“方才你们进得里头,我在外面可是打听了不少。”荀成颇为得意。
倒是姜灼这下有些明白过来,乌黎之子的客忤之症,恐怕在匈奴王庭之时便已做下,后来随着大人们疲于逃命,才延误至今,看来乌黎说什么孩子是被陇西王所吓,还真冤枉了陇西王。
未料人还真不能想,姜灼等人刚踏进驿馆,驿馆的人便来报,说是陇西王来了,让姜灼一回,便过去见他。
一时之间,姜灼便想起陇西王昨晚那句“促膝相谈”,少不得也是好笑,既然人家有请,更何况这一位又是封主,便是懒得理他,姜灼还是要过去的。
不过毕竟是去见男客,姜灼想了想,还是让荀成叫来阿珠,让她跟着自己一块,省得传出去,惹来了是非。
姜灼被领进的是一处花厅,这会子已近夕阳西下,余晖斜斜地穿透窗棱,洒进花厅当中,而此时,陇西王绝无一点架势地靠在门边,倒像是在欣赏远处的落日之景,又像是在等着谁。
“来啦?”瞧见姜灼过来,陇西王明显眼睛一亮,见她抬起胳膊要行礼,陇西王一抬手拦住,口中却没说什么好话:“最烦女人跟本王拱手,不男不女,瞧着眼气。”
阿珠站在姜灼后头,刚准备跟在姜灼后头福身,被陇西王这话弄得一愣,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只好自己免了礼。

 [电影]救国同盟
[电影]救国同盟 [漫画]明星教成男朋友
[漫画]明星教成男朋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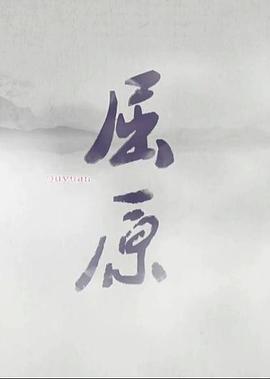 [电视剧]屈原
[电视剧]屈原 [漫画]江山美男入我帐
[漫画]江山美男入我帐 [动漫]小小哲学家
[动漫]小小哲学家 [漫画]绝世武魂
[漫画]绝世武魂 [动漫]一条鱼教画画
[动漫]一条鱼教画画 [漫画]吞噬永恒
[漫画]吞噬永恒 [漫画]寄生告白
[漫画]寄生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