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坐堂
王瑜芙主动出银子给冯嬷嬷治病,倒让姜灼生了几分好感,至于和王瑜芙一起成了冯嬷嬷口中的“天上仙女”,姜灼倒有些不敢当,觉得自己不过尽些医者的本分。
瞧着谭嬷嬷送了冯嬷嬷出门,姜灼自回了药柜,正瞧着药方子配药,郑柯走了过来:“女郎,郑公寻你呢!”
既是师父召唤,姜灼便由着阿青帮了脱去短衫褐衣,净过手之后,随郑柯前往诊堂而去。
郑家药铺逢五、逢十皆由郑无空亲自开堂坐诊,今日二月二十五,少不得诊堂外排成长龙,问诊之人个个手上拿了号牌,伸着头往前瞧,只盼赶紧轮到自己,这其中既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权贵,倒是童叟无欺,不分贵贱,皆排队候诊,只是这队伍未免有些太长。
瞧姜灼过来,正在给人把脉的郑无空指了指旁边一张空几案:“灼灼,以后不用去前头药铺了,”随即又吩咐郑柯:“先将问诊病人带到灼灼处初诊,若有拿不定的,再交老夫之后复诊。”
姜灼吃了一惊:“师父,您这是让我坐堂了?”
郑无空此时正给病人开方子,等写完最后一笔,才抬头道:“你医案、药理已记得不少,如今最缺的是历练,自即日起便随为师坐诊,需记住,病症因人而异,医治之法也要因人而异,绝不可拘泥自封。”
这时有病人被领到姜灼案前,瞧着她还有些稚气未脱的脸,病人不免有些迟疑,退了两步道:“那个……我不急,回头等郑公得空,我再过来。”随即二话不说掉头而走。
姜灼眼看着那人出去之后,宁可重新排到队尾,也不肯听郑柯的,让姜灼先给他瞧病,不免有些哭笑不得。
倒是这时又有一人走上前,大大方方地坐到了姜灼跟前。
对方个头中等,瞧着像是位读书人,身着曲裾深衣,头戴方巾,双眼极是明亮,不过面目清癯,一坐下便不停地在咳嗽。
显然他并不介意姜灼面相稚嫩又是个女郎家,直接将手臂放到脉枕之上,笑着道:“小大夫,今日便麻烦你了。”
姜灼点点头,将手搭到对方脉上,细心探了许久,只觉到他脉相濡缓,颇有滑象,姜灼又让那人伸了伸舌头,只见舌苔白腻,显然脾胃失调。
“老夫患晕症已有三、五年,平素头重、胸闷还多痰,近期发作频仍,时有眩晕,便瞧着眼前总是在晃,甚或还会呕吐,有一回连胆汁都吐了出来,”病人自诉得倒也详尽,最后还补充:“素日也是受不得热,一热便头昏,更不能负重,着实苦不堪言。”
姜灼想想,问了句:“想是先生平素是饕客吧?”
那人颇有些惊异:“小大夫如何得知,老夫除了美酒,便好美味佳肴。”
“先生这病症,乃是痰浊阴滞中焦所致,归根在于饮食不当伤了胃,加之心力劳顿又伤脾,如此水谷不经,聚湿生痰,痰所交阻,以致眩晕呕恶。”姜灼说着,很忆开出了药方。
正好此时郑无空的病人离开,郑无空走到姜灼旁边,倒是冲着那位病人拱了拱手:“没想到无涯兄居然过来了。”
被称为无涯兄的这位立时起身回礼:“郑公,今日在下来复诊,心下生了些谐趣,想要考考郑公这位小徒弟,不过……恭喜郑公,果然得了一位高徒!”
郑无空哈哈大笑:“过奖,过奖,能得无涯兄这般夸赞,想是灼灼的医术倒也差强人意。”
此时姜灼已经开好药方,抬头发现郑无空与那位病人相谈甚欢,明显便是熟识得,更兼正好听到对方在夸赞自己,不免倒有些羞怯了。
郑无空拿过姜灼的方子看了看,并不急着评断,却对她道:“快来见过无涯先生,这一位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乃长安城有名的大家,颇为天下读书人推崇,与为师乃多年好友。”
无涯先生忙摆手:“这‘大家’二字,在下愧不敢当,不过仗着读过些书,在胶东王麾下混口饭吃罢了。”
姜灼忙敛衽施礼,要知郑无空一向忖才傲物,能得他青眼的,必非凡人。
“这半夏白术天麻汤开得不错,”郑无空终于看过方子,点头表示赞同,又补充:“当日为师已为他开过此方,原该眩晕有所缓解,想必这些日子再犯,必是自己停了药……”
“还是叫郑公瞧出来了。”无涯先生呵呵一笑,倒是坦然承认。
郑无空无奈地摇了摇头,嘱咐姜灼:“再加些勾藤,菊花,以增平息内风之力。”
“师父,不如另添一味健脾丸,等无涯先生晕症停了之后,用以扶正固本?”姜灼立时建议。
“郑公,你这徒弟日后怕是不得了,敢有自己想法,确是块良医的好料子!”无涯先生大拍手掌。
有了无涯先生带头,再加上郑无空亲口给予肯定,姜灼后头的病人倒是多了起来,也不知无涯先生是不是闲得慌,居然并不肯走,而是在诊堂坐了一天,直到病人渐少,郑柯又跑过来报,在花厅备好酒菜,无涯先生这才跟着郑无空走了,只留下姜灼独自坐诊。
待见最后一人,正是方才弃诊的那位,姜灼倒是细心的问了病情。
病人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但见姜灼并不芥蒂,这才放胆诉讼病情。
原来此人右侧后背腰腔之内,生了一脓疮,胀痛如灼烧,而如今两腿也肿了起来。
“掀开衣裳给我瞧瞧。”姜灼随口吩咐道。
病人有些迟疑,倒是姜灼笑起来:“即来医病,何至于那么多讲究。”
旁边陪着姜灼的阿青也道:“不叫人瞧伤,如何知道症状,我家女郎都不忌讳,你一个男子何必忸怩呢!”
等病人终于脱了衣裳,阿青倒先“啊”了出来,大概是被巨大的脓疮吓到,姜灼却极镇定,用手小心地触了触,立时听病人疼得大嚎,随后又道自从身上长了这东西,他便寒热不均,冷起来要盖数床棉袄,热起来恨不得跳到三九天的河里泡着。

 [小说]嫡女不善之世子妃
[小说]嫡女不善之世子妃 [漫画]江山美男入我帐
[漫画]江山美男入我帐 [动漫]小小哲学家
[动漫]小小哲学家 [动漫]一条鱼教画画
[动漫]一条鱼教画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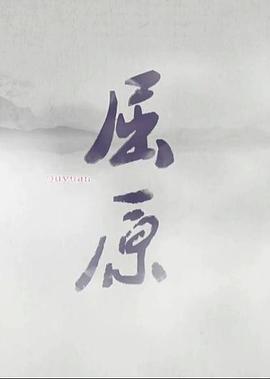 [电视剧]屈原
[电视剧]屈原 [漫画]明星教成男朋友
[漫画]明星教成男朋友 [漫画]绝世武魂
[漫画]绝世武魂 [漫画]吞噬永恒
[漫画]吞噬永恒 [漫画]寄生告白
[漫画]寄生告白